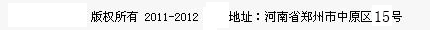▲点击收听▲
今天我们就从仁、智这两德来看仁与智的关系。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智”?如果以仁德为总德,仁必然是包含智的,但是现在我们为了更清楚地来说明全体之德,我们分仁、智两方面,因为在《论语》里也曾经这样分。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又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孔子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这个“仁者”、“智者”大概都从果位上说。所谓果位就是说,他已经是一个仁者,一个智者。
那么仁者以什么来规定?就是“安于仁”。所谓安呢,就是他常住于仁中,安于仁者可以称为是一个仁者。而智者呢,智者只是“利于仁”。什么叫“利于仁”呢?就是他能够知仁的意义,知仁之可追求。所以知者的知,在这里不是一般的知,不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知。当然在文句里面都同样用“知”这一个字,但是,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时候,我们读为知,但是“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它也用“知”这个字,我们就念成“智”。尤其在儒家的教导当中说,“智”是知道的能力,知道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知道“仁”,以知道仁为“智”。你若所知的不是仁,那就不足以是儒家所说的“智”,所以这个智,以“知仁”为核心。佛家将梵文Praj?ā翻译为“般若”,有时候也翻译成“智”,合称“般若智”。不管是讲般若,还是讲智,还是讲般若智,这个智也是一个知的能力,它知道,它认识。但是最严格的翻译法,往往不翻成智或智慧,它翻般若。般若是音译,智或是智慧,是意译。般若本来就是知道的能力、知的能力,当然可以翻成智,但是因为中国儒家的智有特别的意义,所谓的“知者利仁”,所以佛经翻译成“智”恐怕会产生混淆。佛经所说般若,是一种知空或是见空的特别能力,它知的能力有特别的对象、特别的意义;而儒家的智呢,则是知仁的能力、见仁的能力,就是看到仁、知道仁的能力。“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意思就是说知及,也要仁守。从这一章,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问题:请问如果把仁智分开来说成是两德,那么是仁为先呢,还是智为先?我现在不说是仁重要,还是智重要,因为仁重要,智重要。这是不用再讨论的,当然是仁是重要嘛!“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知者利仁”,利于为仁、或是以仁为利,念兹在兹,这一种叫作知者。
仁的意义是智的目的,因此仁的意义高于智,这不用说。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讨论的就是,仁跟智,如果按照孔子说的“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先讲智再讲仁。
所以仁、智这两德放在你实践的这个理论的历程当中,一方面说知及必须仁守,一方面说知及才能仁守。这里表示一个什么意思呢?表示人生的方向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人生先要定一个方向,这个方向谁定呢?这个方向要由“智”来定,所以智先要先及之。而这个分德说的仁——不是总德的仁啊,总德的仁包含一切在仁中——这个分德说的仁呢,就是去把智所见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完成出来,叫作仁守之。我们如果看孟子,他在《公孙丑》这篇第一章讨论知言养气之后,又提到圣人的品格,提到四类的圣人:伯夷、叔齐,治则进,乱则退,这个叫作“圣之清者也”;伊尹呢,是治亦进,乱亦进,这是“圣之任者也”;这个柳下惠呢,是“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对方的染污,对方的不仁不义与我无关,“虽袒褐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是“圣之和”,他能够与人相协和。这三者分别是圣之清、圣之任、圣之和。圣是什么意思呢?圣就是达到了极点,把这方面的品质做到底了,这个也可以姑且说他是圣,因为清也是一种好的品质嘛,清清白白、不受染污。伯夷、叔齐啊,对于他的德行的清白的持守是达到全尽的地步。所以他的清达到了圣的地步,叫作圣之清。圣之任、圣之和,也是类似的意思,但这都是一偏地达到极点。因此最后,孟子又提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时”,是随时,那如果是随时,就是随处、无处不是。无处不恰到好处,无处不是充极圆满,这叫圣之时。圣之清、圣之任、圣之和与圣之时,其实不应该说是四种——孔子是天地的气象,各种兼备——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说有四类,只是其中类它不跟其他三类相比拟,它是综合性的、超越的一类。ENDEND
扫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