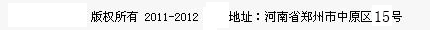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顺治十年五月,洪承畴受命任西南五省经略。
福临认为,清军虽然攻下湖南、两广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云贵尚为南明控制,急需“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结果,只有洪承畴克当斯任。
洪氏遂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
1、洪承畴的权限清廷授予洪承畴敕书规定“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其权限几与汉三王相同,甚至八旗满洲亲贵将军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令;统辖范围包括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即今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六省),大大超过招抚江南时期实际上只辖江南一省(包括今安徽和江苏两省及上海市);事权更加扩大,五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悉听节制”,“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
所行之事,“若系密切机务,任尔便宜”。
便宜行事的权力包括朝野内外文武百官任用“军前及地方”的调动权;所辖范围内各省文武官员的升、转、补、调的行政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将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可以先斩后奏的刑事权。
总之,凡有关军前之事,所欲任用人员,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的钱粮须立即解与,户部不得稽迟。六部几乎成为西南军前专衙,洪氏集军、政、刑、财等大权于一身,戎节之重,一时无出其右者。
从另一角度看,也是清廷面临山穷水复局面,而洪承畴前往湖南,绝无任何妥协余地,背水一战已成定局。
从以后的事实看,洪承畴作为西南五省经略,独掌大权出镇湖南,师老饷靡屯兵坚城,一筹莫展,寸土未恢,不但未受惩处,反而处处得到迁就。
这样的事实,说明这段历史并非如后人想像的那么简单,而是更加隐晦、曲折和复杂。
顺治十年闰六月初五,洪承畴请求拨船50余艘,载随行官兵千余,走水路,而马匹从陆路空驱前往湖广。洪承畴十一月初十日抵达武昌,次年春天三月十二日到湖南长沙。
2、洪承畴的幕府有多牛?洪承畴离开北京前,就提出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战略思想:
“臣受命为五省经略,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但此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
也就是说,最终消灭南明抗清武装是洪氏经略西南的总体目标,具体行动方针则是以政治手段招抚“胁从”为主,以“真剿”的军事镇压为辅,在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及其生存土壤的基础上,通过军事决战夺取最后胜利。
这一思想的提出,表现洪氏对当时形势的把握十分准确、精到,不仅与清廷当时总体战略走势一致,也是战略相持阶段的必然产物。庞大的长沙幕府正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产物。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二日,洪承畴开府长沙,日理万机,十分繁忙。
长沙幕府正式启动,这是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的司令部。
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是经略经制直辖的官员吏目,即长沙幕府的额定幕僚,他们均食俸清廷;二是洪氏从各处延揽的额外幕客,大多为湖南及附近地区的士绅,他们就食于洪承畴。
此外,长沙府及洪氏辖下各督抚提镇参与事务关会者,也可视为幕府成员。因而长沙幕府十分庞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分复杂,来源多样,地位相当重要。
幕府第一个职能是派员有效管辖清军占领的湖南各地。长沙及四周道、府、州、县的地方官,大都由幕府成员出任,这是清廷派驻湖南的第三拨地方官,他们的身份大多为“军前供事”、“军前效用”或“随征”人员,均为洪氏出京携带及一路征召的幕僚。
他们承担了管辖清军占领区的职责,大致包括岳州、常德、长沙、衡州、宝庆、永州、郴州等府。
在洪承畴千方百计努力下,许多湖南及外地流寓、服官士绅先后进入长沙幕府,成为洪承畴的左膀右臂,长沙幕府开始扩大。
这些新入幕成员,或在明朝已有功名,或有不足,但均各有所长,非能征善战果敢之士,即地方上有影响者,甚至在南明身居高位。他们转变立场,进入长沙幕府,体现了洪承畴招抚策略的成功。
其入幕府,承担各种战略任务,不仅为普通民众观瞻马首,且直接投身分化、瓦解抗清武装的活动,为削弱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实现洪承畴既定战略目标,发挥重大作用,湖南的局面逐渐打开。
3、幕府对瓦解抗清武装的作用在长沙幕府中,有专职从事招抚活动的幕僚,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前往抗清武装活跃的地区,进行招抚工作。他们为贯彻洪承畴以政治手段招抚“胁从”为主,军事决战为辅的战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洪承畴利用长沙幕府进行招抚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
第一,弥补了清军兵力不足,在复杂地形中无法发挥战斗力的弱点。
顺治十三年,荆州总兵郑四维鉴于湖北荆门近逼“寇锋”,建议将安陆驻防移至此地,但安陆所属钟祥、潜江、景陵、沔阳等州县,因四面环湖,“素称绿林出没之所”,东、北面黄州、德安,也有“各寨伏莽耽耽思逞”,洪氏只得采取折衷方案,将安陆驻防一分为二,一移荆门,一留安陆。
显然湖北各地抗清武装占据有利地形,打击、骚扰清军,使得清兵防不胜防,守不胜守。不惟兵力不敷,即使拥有优势兵力也无从发挥,“从来满兵所到,贼即败亡”,“但鸟道羊肠,马匹不便驰骤”,湖广总督祖泽远“为此不敢吁控”满兵前来剿贼。
派出幕客单刀赴会,往往可以寓奇于胜,出其不意,收到甚至是千军万马也无法取得的成效,陈宏范等招抚黄州山寨、廖文英招抚连阳八排山寨都是典型的例子,长沙幕府的特殊作用再次显示出来。
第二,削弱对方有生力量。
顺治十三年,湖北南明知府郭子治、知州刘亢等率士民投诚,洪承畴十分兴奋,觉得这不仅“使职多一民而贼少一助”,且“巫夔之间耕凿久驰,竟成荒土,贼之外地无委积可恃,动多掣肘”。
很显然,清军与南明争夺“外地”的斗争,正是相持阶段清军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加强己方力量,为转入进攻阶段奠定军事基础。
顺治十二年四月,娜阳巡抚胡全才全力奉行招抚政策,招到益国公郝永忠部下负责守卫清风寨口路的总兵谢宗孔带领所属人马投诚,部分人员被编入清军,其余给票递送原籍。这既瓦解、削弱了南明武装,也增强了清军力量,便于各个击破,可谓一箭双雕。
长沙幕府的招抚活动,为军事进攻扫清许多障碍。通过这一阶段的战斗,清军逐渐肃清了与云贵抗清武装相呼应、作为湖南战场依托的湖北山寨武装,广东、广西各地的苗瑶武装和抗清基地,取得了较大成果。
顺治十二、三年之间,湖北蕲黄山寨武装、湘粤赣交界的苗民武装已被分化、瓦解,渐至销声匿迹。郧襄一带活动了十几年的姚黄十三家农民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湘东南的“红头军”也渐被肃清,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打击,社会基础也大为削弱。
第三,动摇南明武装军心。
长沙幕府的活动,“既为招抚榜样,更足离散贼心”。削弱抗清武装的军事力量只是洪承畴的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招抚活动,达到“离散贼心”,使对方出现政治分裂。这才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
朱应升,江宁上元人,崇祯十二年举人,入清为颖州学官,出为巡按御史,顺治十年转宝庆府推官,招抚流亡,抚绥残黎,不遗余力,顺治十三年,因岁贡芽茶延误日期被解职。
解职后,他协助偏沅巡抚袁廓宇作分化、瓦解南明军队的工作,“实心招抚”,争取到孙可望部将姜春生、姜和生,总兵王瑞泰、王仁晴、谢成龙、谢才尚及道员孙应赓等投诚。
这一系列投诚事件,是通过血缘、乡党关系的纽带,连瓜带蔓引发出来的,对抗清队伍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
因此,洪承畴深惜朱应升的才干,“檄至军前效用”,其“赞经略洪承畴幕,出谋发虑,动合机宜”。
洪氏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一夕飞骑报敌人入境,公(指朱应升)曰:不鼓渊不整队而至者是敌内江,非犯顺也。迟明,果孙可望崩溃来降,趋经略开门纳款军中,咸以为军中诸葛云”。
4、幕府对军事行动的作用开府长沙之初,湖南几乎是个废墟的世界,“城皆瓦砾,公招降流移,兵民始聚”。洪承畴及其幕府成员首先招集人民、恢复社会秩序。
湖南郡县经过明清战争,户口几乎减少一半。顺治十一年知县傅继说招集流亡,仅得老幼人。桂东知县汪震元下车伊始,招集流亡,全县仅存何时济、李青等63户,“抚养生聚,民气渐复”。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恢复经济是当务之急。长沙幕府开展屯田,征收“洪饷”,贡献颇大。
明代屯田已成制度。有卫所屯田的军屯,移民屯垦的民屯,洪承畴将这些制度酌情应用。接受幕客建议,在湖广军前推广屯田,作为恢复社会经济的基本措施之一,成为当时全国屯田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初抵长沙,洪氏“念赋重土荒,分遣屯田,官给牛、种,岁征子粒,贷其赋三年,增赋十数万而无损于民”。湖南在清初几经反复,饱受战争破坏,经济凋敝,人民逃亡,生产几乎处在停顿状态。
屯田收入可补充军需,这也是洪承畴大力推行屯田的原动力。顺治十六年,洪承畴曾提到“十一年起至十四年止,凡湖南屯田、江西折米及职军前盐利、木利生息,接济军需,各项奏效文册,职俱一时并行督造”,在此不排除直接调拨军前将士从事屯田的可能。
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在可控区域内增收田赋,这即“洪饷”,也称九厘银。
“洪饷”起征时间,各地先后不一,湖北是顺治九年,湖南则以清廷实行有效统治先后为序,宁乡在顺治十一年,多数地方为十二年,如衡阳、清泉、耒阳、安仁等地。湖南长沙府的三项主要税源一民赋、更名、屯卫中,“地亩另派”的九厘饷银在民赋、更名中均有征收,与杂课等都“按亩摊征,分部起解”。南明占领区则无法征收。
顺治十四年清廷将九厘银作为正赋的一个组成部分,列入《赋役全书》中,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明代“弊政”遂成新朝正科。
长沙幕府中大批专门从事运粮的幕客对此应有切身体会。主管湖广军前粮饷的幕僚是洪氏“姻亲”黄志遴。
黄志遴,字铨士,鸥湄,福建晋江人,顺治三年进士,是清朝福建通籍的第一人。选庶吉士,官至少詹事,出为湖广左布政,劝民农桑,以为守令倡。“时经略洪承畴驻楚,督征滇黔,志遴挽运转输,咄嗟立办”,俨然是幕僚领班。
湖广布政使,职掌钱谷,在腹里内地已称繁难,何况非常时期,凡滇、黔两省及广西一省兵饷,都责成转解,数目既多,路途又远,兼以大兵云集,需用更急。因此,洪承畴特意委用“姻亲”子弟担任,以便“多方计算,刻期速运”。
为了粮饷能迅速、及时运抵前线,洪氏还下大力气,“造官船八百余艘”。原署长沙府、后任常德通判的张道澄,仅顺治十二年就赴永州打造扒杆粮船只。
洪承畴在湖广军前,曾多次贩盐,仅见记载的就有三次。私下贩盐,本为违法,洪承畴以“接济军需”为名,大规模贩盐,清廷只开一眼闭一眼。
湖广管理驿传盐法道,与行盐事务密切相关。顺治十二年,湖广驿传盐法道为于时跃,后升任广西巡抚,由分巡上荆南道下三元接任,“湖广用兵之区,更需疏引招商,行盐利民”。
他们两人对湖广军前贩盐之事定然多有措置。
(正文完)
如果有其他关于历史领域的话题或观点可以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第一时间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