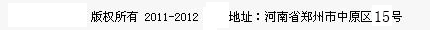宋朝时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而且为政者提倡读书读律,法律思想也较为活跃,一些著名的法学著作相继问世。例如,律学博士付霖撰写的《刑统赋》,将建隆四年颁布的《宋刑统》以音韵的形式编成通俗易懂便于学习的律学读本,并且亲自作注。还有仁宗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孙奭撰《律文音义》和《律令释义》二书。而且,宋人十分注重分析案例,总结实践经验,撰写了《折狱龟鉴》、《棠阴比事》、《洗冤集录》等书。
自觉精神
法律的发展不仅受到经济条件及权力结构的影响,而且,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在法律传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兼理行政与司法的士大夫作为该传统文化的维系和传承者,其活动及意识创造对法律传统的深刻作用。
与西方国家具有职业法学家集团不同,中国古代虽不具有专门的职业法学家,但是在十世纪末到十三世纪中期,古代中国有着那样一群既饱读四书五经、俨然儒雅又能吟诗唱和、熟谙律令、工于吏事的知识阶层,史称之为士。
这个群体通晓文章、经术,具有干吏之才,在教化、行政和司法等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他们出入佛老,援佛入儒,言必中当世之过,行必有补于世,尊奉着“此天下,虽一人,吾往也”的精神信念,更以天下之乐为乐,以天下之忧为忧。
在中国古代,士大夫是礼法文化的传承者。他们不但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度和社会的管理,而且,在法律上,不仅要执行国家法令,更重要的是担当兴教化、定条教之责。就宋代士大夫而论,它的最为显著的时代风貌,是它“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精神。
历史上以“真宗仁宗”之际,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为代表。他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成为宋代士大夫精神风貌的生动写照。钱穆说:“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从自己内心深处涌现的一种感觉,觉得他们应该起来担负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
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这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精神反映到实践上,史学家陈志超先生把它概括为两种现象:一种是一些士大夫将前人断狱的记载汇集成书,如北宋初的《疑狱集》、郑克的《折狱龟鉴》、桂万荣的《棠阴比事》、宋慈的《洗冤集录》。
另一种是一些士大夫将自己所作的判词收集保存起来,编入文章,传于后世。《宋史》卷四一零范应玲本传记载他为官崇仁县时,夙兴冠裳听讼,发摘如神,故事无不依期结正,虽负者也无不心服。后他又任广西、浙东提点,有《对越集》四十九卷,专门收录他的判词。刘后村的文集《后村先生大全集》中一百九十二、一百九十三卷就是他在任江东提刑时所作的书判辑录。
以民为本
早在西周,统治者即意识到要维护政权的长治久安,就需要做到“敬天保民”,“以德配天”。民心即是天心,民意即是天意。“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孟子在孔子“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伟大理想。
人民的拥护是取得和保持政权长久的重要力量,君主治理国家,立法、司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社会的安稳安定,百姓们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富足。宋理学家仍然提倡“民为邦本”的思想,朱熹则认为“民之所欲,皆为致之,如聚敛然;民之所恶,勿施于民”。作为统治者当节约用度,薄赋轻徭,征调民夫之时应不违农时,避免过度消耗百姓物力。
从后村书判《铅山县申场兵增额事》看,刘后村执政为民,即反对官府盘剥压榨百姓,对百姓疾苦深怀同情。其判文曰:“当职旧在江上,见戎帅拈刺新军,必经总所。盖有衣粮然后可以养兵,岂有但知增额,而不思衣粮何处擘划之理?都大司收刺犹可,今检踏官亦得以自刺自添,原額五百,今增三百,县道何以不收坏,百姓何以不焦熬?
备牒都大司,更请参考旧制,立为定额,每刺一名,须下本县取会,如无阙额,不许检踏官員自增自刺,庶几凋县稍可支吾。此判中,后村认为检踏官擅自增額,无疑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对增額之事,他认为都大司当以定額为制,若要增加须得报经本县,否则既易造成检踏官擅自变更原額,欺上昧下又将损伤百姓的利益。判语中对胡乱增额一事深感有害于民,为民之利考虑,后村严格要求本县官员依令而行,不得自专。
《坊市阿张状述年九十以上乞支给钱絹事》书判,也反映出刘后村对百姓的关爱之情,此判为阿张诉官府不给钱粮之事。当其时,朝廷对高寿老人均有恩赏,然在此案中本郡阿张老人的恩赏被官府以银两不足为由剥夺,对此事后村感到非常惭愧,判中语曰“高年之人,支給些小钱絹酒米,此朝廷旷荡之泽也,奈何以郡计艰窘之故而废格上恩乎?”
朝廷对高年老人发给钱粮絹酒是为恩泽百姓,然此郡却以银两不足为由不再执行此项规定。发放的钱粮虽少,却是朝廷对百姓的泽被,更是民益,此等有利于民之事,后村认为不应当无正当理由而剥夺,从判语之中看虽是在此彰显朝廷仁厚,但其中对民生利益的关心之意透过判语跃然而出。
书判《安仁县妄摊监钱事》,其判文曰:“吴兴四父子乃制牒所不追究之人,本县凭何追扰?可見纵甲摊乙,又纵乙摊丙,为民父母,宁忍之乎?帖具因依申。”从判文之意可见吴興四人本不该摊派监钱,然现实中他们四人仍被摊派监钱一事,此事诉至官府,刘后村认为监钱摊派官府不可随意为之,作为百姓的父母官当爱民如子,岂能随意剥夺百姓,对这等滥加摊派之事不可姑息,申令治下官司严肃处理。
证据客观理性
在司法中法官当尽力追求诉讼的公平公正,要做到公平公正不仅要求有公之心,以公去私。有公心方能客观的审视案情,理性的作出判断,案件的审理离不开调查取证,案件的真相也有赖于诸多证据的辅助。
在后村的书判《争山妄指界至》,俞行父与傅三七争山之讼,经审理本已定夺,然行父后又不服,妄图乱其是非,官府欲对其重断之时,此时又有祖主簿为其申说冤屈,事情发展到现在,后村不得不再次审查此案。经派县尉亲至地头,查明原委,发现双方所争山地,无有干系。其实是俞行父妄图占据他人山地而造出此等讼事。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俞行父更妄图以利贿赂官府,幸得县尉秉公执法,不使其行得逞。本案中,为查明情状,对双方争议之物经历了严格的勘查,才使事实澄明,促成最后的决断。在审理这一案时,刘后村为了查清事实,“遂委县尉定验”,县尉奉命“亲至地头”勘验,勘验出的结果显示俞行父的山与傅三七的山,两山之间各在两处并不相邻,中间还隔着一堑,俞行父本就无理。
勘验检查是宋代官府搜集证据的重要方法,证据的搜集、鉴定对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西周,官府在处理民事诉讼的时候
就已经注意到证据的重要性,凡“民讼,以地比正之”,即审理诉讼时,要以邻为证。进入唐宋,证据制度在司法审判中越来越得以重视,在唐朝的法律中已有较为详细的规定。至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加促进了这一制度的发展。
具体表现就是契约制度的快速发展和完善,社会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契约文书,如在民事交易方面关于货物买卖、借贷、租赁以及产业的抵押、典卖、绝卖等方面发展的相当完备,法律上对这些契约类型也做了具体严格的规定。
《干照不明合行拘毁》一案,本案中潛彝买下仔贵的荒田,后仔貴赎回之时,发现契约内容为人攥改,本该是荒田却变成了另一处荒地。荒田与荒地之间并无一同,荒地的契约应该是另有其契书,不与仔貴荒田契约有干系。所以,本案即是有人故意撰造田契,意图骗人田产、夺人产业。案件审理中根据查明契约这一重要的物证,最终厘清事实,将犯事者拘捕入案。
民事诉讼当中契约有法律上的证明力,契约在宋代时又被称为“干照”,涉及到田地、房屋等大型交易或小额财物的典当、典卖交易均要订立契约,而且交易的成立完成还必须有前一次所有权转移的契书,即“上手干照”。
典卖田地的契约不但须要经过官府印押,而且在这过程中官府也要收取一定的税額。而经官府印押的契约称为赤契,具有法律效力,是买主在法律上取得某项财产权的凭据,“田产”典卖,须凭印券交业。
若券不印及未交业,虽有输纳钞,不足据凭”。在此案中,判文中首句即说道:“置卖产业,皆须凭上手干照。”判中以干照为据,查明两处田地并不相干,且潛彝父子恃强凌弱,在乡间骗人田产,巧取抢夺之事不可胜数。
结语
在以上两案中,不论在审案中进行勘验事实现场还是查证契约,皆是为了获得案情的真相,客观是审理案件的首要原则。而关于契约的成立条件、书写格式、保存方式等方面在法律上都有明确规定,法律的详细规定保证了它在诉讼中与其他证据之间证明力的高下之别,官府在审理诉讼时,往往根据契约便可直接作出裁判。
虽民间私约难免出现各种假伪,然经官印押的契书具有很大的可靠性,“交易有争,官府定夺,止凭契约。”“大凡官厅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官司理断交易,且当以赤契为主。”这两份书判,一是通过勘验取证,二是以契约为证,案件的审理均是依靠客观可靠的证据。
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联系删除!